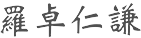我要來談談漢藏佛教交流的重要性,個人認為是我寫過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這篇可能會被罵,也許兩面不討好,但我自認一直以來的初衷就是講事實,實事求是,所以這些世間的讚毀也就無法顧慮到了。
在講這個主題之前,我得先談談自己的背景:我出身漢傳佛教,許多老參聽過的漢傳佛教道場與大德我都曾經親近,更在漢系佛教僧團中受過訓練,當過維那、悅眾,五堂功課等都是家常便飯,也曾努力鑽研過許多漢地的經論與著作。
之後,我在藏地噶瑪噶舉派與法王子蔣貢仁波切同班接受佛學院集訓六年,個人酷愛辯經,在學院求學的頭三年更是孜孜不倦,晚上不曾臥床睡眠、都是在看書的過程中不敵睡意而直接坐著睡著,辯經過程中也曾因過度激動與營養不良等原因昏倒、血尿等多次。
說了這麼多,是想要表達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自認說出來的話有一定的公正性,希望能夠為大家釐清一些想法。
很多華人在佛教圈多年之後接觸到了藏傳佛教,旋即被其佛學院系統所吸引,或年年參加請法團到印度在某些大師坐前聽受五天到十天的某部大論,或努力地學習藏語想要懂得辯經、上佛學院,這些對於法的欲求都是非常值得讚賞的。然而,在此同時,大家都會或多或少的看不起漢傳佛教,認為那是「顯教」、主張「藏傳佛教的系統中早就有顯教的訓練,漢傳卻沒有密教的功德」、「漢傳佛教只有迷信,沒有教育。」等等。
也有許多人在台灣想要引入藏傳佛教的佛學院訓練體制,甚至有些人認為諸如菩提道次第廣論等著作非常殊勝,認為那比漢傳一切典籍還有次第、規矩,嘗試在台灣實踐五部大論的教學,聲稱要建立來自那爛陀的清淨傳承。
這種「藏傳佛教體制至上」、「漢傳佛教經論不足」的想法,是種徹頭徹尾的錯誤。
漢傳佛教現代訓練人才的體制的確有所不足,主要是在邏輯性的訓練上不夠扎根,但是其底蘊所含藏的寶藏實際上是藏傳佛教所恰恰欠缺的。
漢地從公元一世紀就開始了譯經事業,直到十一世紀為止,大量的各人種之譯師們將印度的經論帶到漢地,由當時全國菁英中的菁英組織數十到上千的大眾譯場翻譯與審對。而藏地直到八世紀才開始譯經,基於當時文化教育不普及,譯經大多由少數的一位藏族譯師與一位印度學者合作完成。
華人重視歷史,每位譯師幾乎都會寫下紀錄,是研究當時佛教發展狀態的寶貴史料,在這方面藏人們遠遠不及,許多的傳說與佛苯互相影響等狀況都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淹沒,無法爬梳其原貌了。
以上的說法可能不夠清楚,我就舉幾個例子如下:
藏人自稱接受了那爛陀一切法教的清淨傳承,認為佛教的宗派只分成四派(有部、經部、唯識、中觀),但漢地的文獻清楚的記載了小乘十八部派,大乘的諸派差異。
就算是在這四派的主張上,有部思想最重要的根據「大毘婆沙論」、經部的根本論典「成實論」都是藏文中所沒有而早已翻成漢文的(民國年間才有法尊法師將毘婆沙論翻成藏文),唯識的狀況更是有趣:唯識的演進包括了安慧的古唯識與護法的今唯識,安慧一系又分成了主張九識與八識等不同的學說,這些都被完整保留在中文裡,而藏文文獻對於這些發展過程的記錄只有安慧與其弟子調伏天的兩本著作而已。
儘管藏地各派都無比崇尚中觀宗,但藏文中卻也沒有中觀的百科全書-大智度論,而受到各派奉為頂嚴的應成派月稱,卻反而不曾被注重歷史的任何一位漢地譯師或早期的藏族譯師所提到,根據現代考證其學說從來不曾在印度成為主流。
從密教角度來看,儘管藏地保有了大量的密教文獻,但由於其不重視歷史紀錄的慣性,使得研究變得極難實踐,反倒是從漢地大師們的紀錄中可以看到一些密教發展的痕跡(諸如密教是在約莫公元640年進入那爛陀寺)。
總之,漢地保有了大量絕無僅有的寶貴文獻,而基於華人重視歷史的精神,我們能夠透過其紀錄建構起當時印度佛教的完整發展過程,這兩大特質是藏地所不具備的。
反觀漢地,藏地除了承接了印度晚期中觀與唯識派合流-中觀瑜伽行派的一切理論(此為漢地所無)外,更傳承了印度重視的辯思精神以及梵文原典,這兩點正是漢地所欠缺的。
從民族性來看,華人崇尚「圓融」,喜歡把所有的宗派理論和稀泥,這對於辯思訓練來說是致命的傷害。而藏人喜歡把所有的理論蓋成一棟房子,無法接受其差異多元性,努力證明種種理論只是同一個體系中從下到上的關係(道次第理論是明顯的例子),再將自己的宗派列為最高的層次,這樣的習慣則會嚴重地障礙文獻研究,無法客觀地評判每一個看法的差異。
所以,漢藏佛教的合作可以創造雙贏的結果:將漢地寶貴的文獻與紀錄翻成藏文,以拓寬藏地學者的視野,讓他們能更清楚事實的發展。另一方面則將藏地的辯思訓練引入漢地,讓漢地佛弟子在接受訓練之後,能夠去研讀母語中的寶貴大論,這樣對於兩方的佛弟子們在研究印度佛教真髓的過程中將有無比的利益。
就算我們無法如此,我認為了解漢傳佛教的功德,不要自以為學了藏傳、學了密教就輕視他人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僅僅因為要尊重對方、更重要的是其實對方有許多我們不具有的優點,雙方平等,沒有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