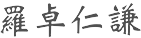近期有不少佛教大師離世:
影響全球的一行禪師、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耆老多智欽仁波切,最讓人震驚意外與悲痛的、就是第三世敦珠仁波切的圓寂,他才大我4歲、剛過而立之年,他的出身與學習歷程,讓他絕對是寧瑪派未來的最高精神領袖,卻英年早逝,讓我輩中人不捨、惋惜與悲痛。
大師們的離世、本來就是讓人難過的一事,但對我來說,我看到的、感到的,覺得值得難過的其實有更深遠的一個層面,就是佛法人才的凋零、佛教領袖的一代一代謝去,
最重要的是:佛教人才的培養非常不易,成本極高、但收益(若可以這麼稱呼它的話)極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佛法身為自詡最為「依法不依人」、最為不重視偶像崇拜、最為重視智信而非迷信的宗教體系,卻弔詭地出現最多、最系統性的「大師情節」:
不論是在漢傳佛教、藏傳佛教或南傳佛教,崇拜神僧、崇拜活佛、崇拜大師的情節,是迭代性地一直發展,並非個案、而是「系統」。
我們先看看別人:一神教的體系中,所有人都是匍匐在神的腳下、就算是高尚的宗教人士,其權威也是來自「神權」的賦予、而非自己天生具備權威。
他們的宗教領袖本質上也是個凡人、大家尊敬與崇拜那個角色,往往不是因為那個「個人」而是那個「職位」。
萬靈信仰與多神教體系中,雖然時不時會出現一些神蹟領袖、或是口才便給的傳教者,但這種信仰體系本身就沒那麼強調智性,其次這種角色的出現,往往是個案、個案的,而非「系統性」地出現。
姑且不論這種「大師情節」與崇拜,是否符合佛陀的教義,我個人認為這對佛法的傳播、絕對是一大障礙,原因在於這種「高度中心化」的發展方式,會讓那個作為大師之人壓力極大。
另一方面則是它非常脆弱:稍帶不尊敬地說、看看現代藏人普遍焦慮於後達賴喇嘛時代,就可以從此中看出端倪。
佛教系統的「組織方式」發展,一直都是「中心化」發展:整個組織的權力,不論是話語權、詮釋權、宗教權、經濟權等,都高度「集中」於中心:活佛、大師、神僧。
中心化的體制下,人的行為「自然而然」變得以服從為主,畢竟人人只向宗教權的來源負責、也只傾聽詮釋權的源頭,所以整個組織幾乎都是由這一個「中心」在掌控。
這會帶來什麼問題?首先如前所說,那個「中心」會承擔高度的壓力跟不安定。
其次,這個組織非常脆弱:整個體制必須花費大量的成本來穩固、養育這個核心,但這個核心一旦出現變數,這些成本極有可能就付諸流水。
我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情如此敏感?因為我親自見證了,一個龐大的僧團體系,將其所有成本傾注在養育新一代的核心仁波切身上、並對其寄與厚望。
結果是,仁波切從小承受著莫大的壓力與矛盾,但這個矛盾是無法得到緩解的,它只會隨著時間的進展、因為權利不停往中心集中,而讓矛盾與緊張升高。
最後,仁波切撂了擔子,直接與僧團正面對立,所有的培育過程所投入的成本,不但是付之東流、更幾乎可說是完全白費,可見整個體制脆弱之至。
其實這種情況不但存在於所謂的「核心化」之仁波切、神僧、活佛身上,我們只要來到一個基礎的層面觀察,就可得出類似的結論:
我自己過去在印度讀書的教派中,同屆入學的佛學院學僧大約有5–600位,能夠完成學業的可能不到1/10、然後完成學業後「有能力任教者」可能又只有30%,而這些任教者中、有智識能夠將佛法推廣到新的群體中的人,可能又只有1%。
整體換算下來,這個「弘教有效」的良率是萬分之三。
你可能會說:「這個比例算不錯了啦!何必苛求?」但這就掉入一個邏輯悖論裡:
我們都說,佛教的錢是「十方財」、必須善用與專款專用,我是不知道任何一家市面上的公司,會接受自己的投資只換來了0.03%的績效。
或許你又會說:「雖然只有0.3%,但只要培養出一個人、就能影響很多人呀!」沒錯,這是事實,但這就是「中心化」思維:想透過一個中心的「神人」來影響一堆人的思維,又會回到上面的邏輯死題裡。
所以,我在我們 解脫Mokshah在做的第一個重要改革,就是「去中心化」的佛教組織方式:舉例來說,我們教團的所有修法活動,都不是我個人去主持的,我把時間花在整理教材、設計編排方式、設計學習制度,讓大家可以在最低成本的情況下、學到最有脈絡與效率的佛法體制(這些設計邏輯之後再慢慢分享。)
整個去中心化的核心,是「權利」的重新賦予,我們至少推動兩個制度:
一、宗教權的如理賦予:從人治走向法治
仿間常看到的情況是,如果某人具備某種頭銜、它就「天然」得到宗教權,能夠有權利在冥陽個層面上利益他人,但是這種「宗教權來自頭銜」的思維模式,本身就是一種「中心化」的思維模式,是人治、而非法治。
我們教團之中,依照傳承、依照古老的規範,要求行者遵循「規則」:佛陀與祖師們告訴我們,宗教權的力量,來自「持戒」與「禪修」。
所以,我將心思花在建立受戒體制、誦戒體制、戒律學習體制,以及禪修學習制度、閉關制度,任何依循這個制度完成之人,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你去行使你的宗教權,諸如現在在度母之家服務的法工,就是如此一位一位培養出來的。
我們依循、建立並守護制度,將正統佛法的內容透明化。
二、詮釋權的如理賦予:從理論走向觀察
如果我們畫一條線,一端是「理論研究」、另外一端是「觀察現實」,你覺得佛陀本人站在哪一端呢?
可想而知,佛陀是站在觀察現實那一端的,這種傾向在《聖典》的《大記詠》中明確可見、在《阿含經》系統中也清楚不已:佛陀揚棄繁瑣厚重的理論論述、重視現實生活的觀察所得,這也是龍樹在《中論》中所提及的精神。
所以, 解脫教團的學習制度中,佔了學員70%時間的是討論反思:當一個教團的核心學習體制,如傳統佛教一般、是由「中心」的法師/老師來傳遞教義,其他人都點頭稱是且鸚鵡學舌時,會導致兩種結果:
a.老師獨佔了詮釋權,並且為了穩抓其話語權而走入繁瑣厚重的理論高塔。
b.弟子們失去「自由思辨與觀察」的佛法核心意義,因為他的「知識」必須由老師賦予。
其結果就像我前陣子看到的一個段子所說:常識就像氧氣一樣,越高位的地方、空氣會越稀薄,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佛教領袖的言論、觀點和論述,似乎還停留在古老的過去。
最重要的是、這種傾向「背離」佛陀的法教!因此,解脫教團的學習制度中,小組討論、將日常所得與觀察,拿來檢視與討論至為重要,教學者提供「定錨」,讓整個討論不偏離佛教的核心,此外的其他詮釋權、討論權、討論所得與觀察所得,完全是自由發生的。
當然,我們還做了更多更多細緻的工作,但這兩項的調整、個人認為是佛法中的一個重要改革起步:佛法組織體系,從中心化、走向去中心化,也是我一直在推動、所謂「佛教改革」的核心所在。
我一直在推動佛法體制的全面性改革,務求讓佛法接觸到更多人、更現代、更生活,回到其原始的樣態;其中,除了軟體的這些制度性改革之外,硬體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今,我正在建立全球第一座全華語的藏傳佛法閉關訓練基地、台灣岡波聖地,透過一個又一個的募資案,一方面讓這些計劃得以步步實現,一方面也讓有識者的支持不是只是支持、而能得到更多層面的福德回饋。